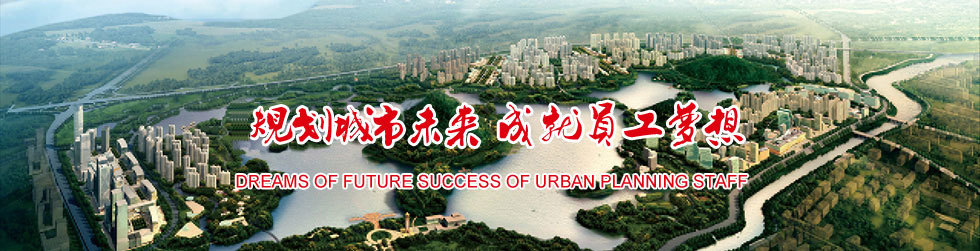濟(jì)南市規(guī)劃設(shè)計(jì)研究院
地址:濟(jì)南市高新區(qū)舜華路2000號(hào)舜泰廣場(chǎng)1號(hào)樓西翼
電話:0531-86910650
郵編:250101
郵箱:ghjghy1380@jn.shandong.cn
消極規(guī)劃|理解城市生長(zhǎng)的邏輯
來(lái)源:澎湃新聞 2020-07-29
作者:吳文媛
斯皮羅·科斯托夫(Spiro Kostof)在《城市的形成》(The City Shaped)中討論了城市的由來(lái):“城市是由人,并且為人而建的。它們所處的地域位置是由人來(lái)決定的,而不是不可抗拒的物質(zhì)操縱的結(jié)果”。
中國(guó)30年來(lái)的城市化實(shí)踐呈現(xiàn)出的經(jīng)驗(yàn)是:一個(gè)區(qū)域建設(shè)的目標(biāo)越是單一,就越不可能將它當(dāng)作城市來(lái)討論,規(guī)劃圖上圖解式的城市,幾乎是空間夢(mèng)想者編造的故事,他們想要復(fù)雜豐富的城市結(jié)構(gòu),卻不想要與之共生的問(wèn)題、壓力和多變性。
所有空間上的“理想城市”,都會(huì)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人性,如果希望讓人的本能發(fā)揮效力,那么本能將抵抗所有的控制(包括規(guī)劃),并因著本能的多樣和變化,在空間中觸發(fā)無(wú)數(shù)的偶然性。而以更消極的態(tài)度和方法處理空間規(guī)劃時(shí),城市才更貼近于日常生活的理想。
理解城市生長(zhǎng)邏輯的案例
深圳的海洋新城項(xiàng)目代表了我們對(duì)于未來(lái)城市的設(shè)想:
第一,它不是原有城市秩序的新拓地,而是未來(lái)城市模型的生長(zhǎng)核;一般而言,新城是沿著老城主要道路而拓展的新開(kāi)盤(pán)區(qū),而海洋新城則反向成為未來(lái)城市的一種結(jié)構(gòu)邏輯——由一個(gè)生長(zhǎng)核,長(zhǎng)成未來(lái)的城市。
第二,它不是城市現(xiàn)有設(shè)施系統(tǒng)的新負(fù)擔(dān),而是城市未來(lái)代謝系統(tǒng)的源代碼。一般建設(shè)新城時(shí),老城要增加一定的水電供給和污水處理,以形成城市總能耗的增量,而海洋新城將有一套新的代謝系統(tǒng),而這套代謝系統(tǒng)是一個(gè)源代碼——它有可能修正原來(lái)的循環(huán)系統(tǒng)(能源、水等)。
第三,它不是汽車(chē)城市的“任天堂”,而是傳統(tǒng)人居生活的超鏈接。汽車(chē)不再作為城市設(shè)計(jì)的主要結(jié)構(gòu)邏輯,而是要還原人的街道生活尺度,滿足傳統(tǒng)的居住及交往等需求。
在海洋新城,我們構(gòu)想了一個(gè)功能復(fù)合的超級(jí)堤壩:其一,將干線車(chē)行道路置于堤壩之下,形成連續(xù)的外環(huán)堤壩與堤下車(chē)行環(huán)道的組合,內(nèi)部不再需要連續(xù)性道路,只需分區(qū)塊接入堤下車(chē)行環(huán)道即可;其二,復(fù)合堤壩是人與自然的過(guò)渡與緩沖帶,在海洋一側(cè),有更為平緩的潮間界面,給水陸交界處的生物提供更多棲息空間,而在城市一側(cè),有可連通至建筑頂部的多層級(jí)的綠化與活動(dòng)空間,提供親近自然和海洋的休閑場(chǎng)所。
超級(jí)堤壩示意。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
在堤下車(chē)行環(huán)道的基礎(chǔ)上,將接入各區(qū)塊的車(chē)行支路亦全部埋入地下空間,與規(guī)劃軌道交通形成配合,地面空間則全部釋放作公交與慢行專(zhuān)線,從而搭建片區(qū)的綠色交通系統(tǒng)。地面公交只在完全建成后才有必要,一開(kāi)始是沒(méi)必要的。
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步行,每個(gè)組團(tuán)、每個(gè)城市區(qū)塊都是步行可達(dá)的單元。在封閉地下車(chē)行系統(tǒng)里,最先實(shí)現(xiàn)的是無(wú)人駕駛或汽車(chē)共享,車(chē)可以一直運(yùn)動(dòng),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小的停車(chē)場(chǎng),換乘點(diǎn)都在和外部的連接點(diǎn)上,出去后才融入城市大系統(tǒng)。
可以對(duì)比一下原來(lái)的規(guī)劃,它將城市的網(wǎng)格道路系統(tǒng)全部延伸進(jìn)片區(qū),在這種秩序之下,一塊塊用地還沒(méi)填滿時(shí),就必須先修完整的道路。而我們的規(guī)劃,脫離了這種網(wǎng)格秩序,類(lèi)似于細(xì)胞的島嶼,可以一個(gè)單元一個(gè)單元地生長(zhǎng),長(zhǎng)一個(gè)單元再修一條路進(jìn)去,每個(gè)單元的生長(zhǎng)過(guò)程保持了完整性,片區(qū)就像一個(gè)生物體在生長(zhǎng),骨骼長(zhǎng)一寸再長(zhǎng)點(diǎn)肉,具有極大的彈性。我們期待這種全新的空間生長(zhǎng)邏輯可以作為示范,慢慢影響整個(gè)城市。
網(wǎng)格秩序的改變
消極規(guī)劃需要規(guī)劃管理上的變革
如果不考慮社會(huì)、生態(tài)和技術(shù)、資本的局限,規(guī)劃就可以無(wú)止境地追求美輪美奐,但是如果不得不面對(duì)各種復(fù)雜的現(xiàn)狀和有限的資源,并要在其中編出秩序,則極大考驗(yàn)價(jià)值觀和對(duì)空間工具的運(yùn)用能力。
從方法論角度來(lái)說(shuō),消極規(guī)劃是可以通過(guò)日常的積累不斷豐富的,畢竟每個(gè)城市的問(wèn)題猶如個(gè)體差異,但是管理的變革趨勢(shì)應(yīng)該是收縮規(guī)劃的權(quán)力,從功能和空間的100%設(shè)計(jì)向“分區(qū)塊有限設(shè)計(jì)+底限管理模式”方向發(fā)展。
有限設(shè)計(jì)模式
所謂分區(qū)塊有限設(shè)計(jì),是針對(duì)現(xiàn)在城市中心與郊區(qū)采用統(tǒng)一管理強(qiáng)度的辦法,使得城市勻質(zhì)化,難以自發(fā)累積形成價(jià)值更高的類(lèi)城市中心區(qū)塊,而邊緣地塊又沒(méi)有應(yīng)對(duì)變化的靈活性。所以,規(guī)劃應(yīng)該從中心向邊緣遞減設(shè)計(jì)的強(qiáng)度,例如中心區(qū)只做60%的設(shè)計(jì),將道路、公共開(kāi)放空間設(shè)施做100%的設(shè)計(jì),功能只做近期和必需的40%的設(shè)計(jì),只對(duì)50%地塊做出限高設(shè)計(jì);到了城市邊緣地區(qū),只對(duì)必需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管理做100%的設(shè)計(jì),建設(shè)規(guī)劃只規(guī)定20%的設(shè)計(jì)等等。
而底限管理可以分解如下:從單位地塊功能管理變?yōu)椤盎竟δ? 彈性指標(biāo)”管理(如商務(wù)功能地塊的指標(biāo)為:50%商務(wù)+20%居住+20%商業(yè)+10%自主);從容積率管理變?yōu)椤案采w率+彈性限高+形態(tài)”管理;從道路紅線外擴(kuò)管理,變?yōu)椤盎就ㄐ泄δ?道路設(shè)施+邊界互換功能”;從道路定位定線管理,變?yōu)橹芬韵?“密度管理+導(dǎo)則指引”等等。
比如容積率的問(wèn)題,同樣大小的地塊,在相同的容積率下,建筑面積一樣多,街區(qū)形態(tài)卻可能完全不一樣,所以單一容積率的管理其實(shí)毫無(wú)意義。
相同容積率下的不同街區(qū)形態(tài)
目前的容積率管理最容易建高層,因?yàn)樽詈?jiǎn)單。其實(shí)只需要做形態(tài)管理,不需要管理其他東西。比如道路紅線其實(shí)是個(gè)可調(diào)適的空間,實(shí)際上很多道路不需要那么寬。只要規(guī)定基本的交通空間,如中間有兩個(gè)車(chē)道是必須的,其他空間都可以彈性管理。這樣一來(lái),如果在某處做公共的殘疾人設(shè)施,就可以突破道路紅線,讓它更接近公交車(chē)。
再比如,一個(gè)商業(yè)建筑,如果只規(guī)定商業(yè)部分的停車(chē)空間,那么有可能自己發(fā)展出其他的停車(chē)空間,還有可能在屋頂發(fā)展出一個(gè)幼兒園,甚至首層還可能有口袋公園。
設(shè)計(jì)師需要敬畏自然和先驗(yàn)理論嗎?
古往今來(lái),都不缺乏原始自然的崇拜者。自然崇拜和權(quán)力崇拜具有同構(gòu)特征,都要構(gòu)建一種不可追問(wèn)的必然性,對(duì)于看不透、打不贏,又?jǐn)[脫不了的對(duì)象,就用同強(qiáng)權(quán)者的相處方式同等對(duì)待——將其神秘化,賦予某些神圣屬性,并設(shè)定各種邊界和規(guī)范約束著人類(lèi)的行為。人類(lèi)能有今天的成就,來(lái)源于對(duì)權(quán)力和自然的不斷抗?fàn)?、學(xué)習(xí)、妥協(xié)乃至超越。
而規(guī)劃師在著手展開(kāi)空間規(guī)劃設(shè)計(jì)時(shí),對(duì)于常識(shí)的可靠認(rèn)知,比任何先進(jìn)的理念更重要。人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,是最基本的常識(shí)。浩瀚星空,日出月落,鮮花盛開(kāi),清風(fēng)拂面,正是因?yàn)橛腥祟?lèi)的需要,這些才顯得彌足珍貴。
我們還應(yīng)謹(jǐn)慎對(duì)待依賴(lài)于人工系統(tǒng)的各種設(shè)計(jì)理論,很多先驗(yàn)理論的發(fā)展背景有別于中國(guó)當(dāng)下很多場(chǎng)地的現(xiàn)狀。
如很受追捧的TOD公交導(dǎo)向型開(kāi)發(fā)模式理論,是美國(guó)新城市注意規(guī)劃師彼得· 卡爾索普于1990年代提出的。簡(jiǎn)單地說(shuō),該模式就是在軌道交通的樞紐站形成高密度開(kāi)發(fā),從而節(jié)省土地,減少對(duì)私家機(jī)動(dòng)車(chē)的依賴(lài)。在這樣的巨構(gòu)綜合體內(nèi),商業(yè)是扁平化的,稍有差異的是面積、裝修和價(jià)格;居住更是簡(jiǎn)化到屈指可數(shù)的幾種單元;當(dāng)然,出行模式也是高度相似的。這種固化的業(yè)態(tài)混合把商業(yè)可能的結(jié)構(gòu)層級(jí)簡(jiǎn)化到極致,卻不能隨著時(shí)間推移產(chǎn)生豐富的演變。
這種極簡(jiǎn)模式不能隨著時(shí)間推移適應(yīng)、變化、耦合出新的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。而城市發(fā)展所需要的城市密度不僅指建筑面積的增加,更包含了就業(yè)方式多樣、人口關(guān)聯(lián)性復(fù)雜、文化特征多元等內(nèi)容,而這些是需要時(shí)間來(lái)養(yǎng)成磨合的。
其次,我們都不能否認(rèn)人造系統(tǒng)是有壽命周期的,在所有歷史存留的構(gòu)筑物和人工系統(tǒng)上,隨時(shí)可見(jiàn)人類(lèi)力量持續(xù)的干預(yù):修繕、翻建、更新、改造……正是人類(lèi)意愿、財(cái)富和技術(shù)的持續(xù)的灌注,才使得這些系統(tǒng)得以維持。
我們無(wú)法計(jì)量人類(lèi)花費(fèi)了多少心力來(lái)建設(shè)和維持歷史長(zhǎng)達(dá)上千年的城市,并走到了今天。城市發(fā)展可參考的不是不變的標(biāo)準(zhǔn)和理論框架,而是解決人的需求,并不斷增加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連接。
這些連接看似日常且平凡,卻是長(zhǎng)期歷史磨合下的最佳狀態(tài),具有高度的合理性。這種關(guān)系應(yīng)被視為重要的社會(huì)資本,只有在保留理性?xún)?nèi)容基礎(chǔ)上的增量才是真的發(fā)展。
分歧和共識(shí),哪個(gè)對(duì)實(shí)現(xiàn)規(guī)劃更重要?
民主是一個(gè)困難的制度,而且文明程度越高,個(gè)體的意志就越自覺(jué),實(shí)際上意見(jiàn)分歧是城市問(wèn)題的基本面。由此有人判斷,在規(guī)劃中公眾的參與是不可能達(dá)成共識(shí)的,公眾參與的過(guò)程意義大于公眾對(duì)產(chǎn)生決策的期待,更多是在過(guò)程中獲得療愈。
持這種意見(jiàn)的業(yè)內(nèi)人士眾多,因?yàn)閷?shí)踐中達(dá)成共識(shí)的難度確實(shí)很大。在若干場(chǎng)合也常聽(tīng)到有人呼吁,深圳應(yīng)該放棄進(jìn)取式的發(fā)展模式,這是典型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思路。而將“達(dá)成統(tǒng)一的共識(shí)”作為目標(biāo),就是有悖于城市最重要的多樣性精神。
就拿公車(chē)悖論來(lái)說(shuō),車(chē)上和車(chē)下的人,很容易就增加一輛公交車(chē)的提案達(dá)成共識(shí)。人是具有能動(dòng)性的,社會(huì)是有持續(xù)調(diào)適能力的,“滿足”因此也是不斷在各種需求中擺動(dòng)的。達(dá)成基本價(jià)值共識(shí)需要利益相關(guān)者的文化背景具有完整性和持續(xù)性,這在城市高流動(dòng)性背景下就必然埋下了分歧。
在多次組織公眾參與規(guī)劃實(shí)踐后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利益是無(wú)法統(tǒng)一共識(shí)的,只能通過(guò)博弈,達(dá)成不同程度的妥協(xié),或者在每個(gè)問(wèn)題排序比重不同的個(gè)體間找到妥協(xié)的可能。而一個(gè)好的社會(huì),個(gè)體應(yīng)該能夠各自表述正確,這才能幫助規(guī)劃在端源解決問(wèn)題。
總之,將規(guī)劃的權(quán)力逐步讓渡給研究和發(fā)展的自發(fā)性,才會(huì)解放出城市的多樣性。
(作者吳文媛系深圳雅克蘭德設(shè)計(jì)有限公司首席規(guī)劃師。本文部分內(nèi)容經(jīng)授權(quán)轉(zhuǎn)載自《國(guó)際城市規(guī)劃》2019年第6期,原標(biāo)題為《消極規(guī)劃:直面城市加密的日常生活》,經(jīng)刪減編輯。)
責(zé)任編輯:馮婧
校對(duì):劉威